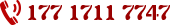刑事实务
美国刑事被告人获得律师有效帮助制度及其借鉴
作者:李耀辉 河北世纪方舟律师事务所
在美国的刑事司法程序中,刑事被告人获得律师有效帮助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宪法性权利。美国宪法第六修正案规定,在一切刑事案件中,刑事被告人享有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并且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经过五十多年的判决和判例丰富发展了被告人获得律师有效帮助权。目前,我国对刑事被告人获得律师有效帮助问题的研究基本处于空白状态,刑事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只是程序意义上被告人享有律师帮助权,而被告人在效果上是否获得律师有效帮助未予关注。随着刑事诉讼中辩护权和人权保障的进一步发展,我国应当借鉴美国的刑事被告人获得律师有效帮助制度,在理解该项制度内涵、宪法标准和具体操作的基础上考虑是否逐步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引入刑事被告人获得律师有效帮助制度,本文通过对美国刑事被告人获得律师有效帮助权的研究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有所借鉴。
一、刑事被告人获得律师有效帮助权的理论基础
根据宪政理论,宪政的精髓是限制国家权力和保障公民权利。在现代宪政国家中,刑事诉讼使得打击犯罪不再具有绝对的意义,不再成为刑事法律的“帝王条款”,不计代价、不择手段、不问是非的刑事诉讼方式应当受到严格的禁止。在宪政社会,任何公共权力的建立都是为了保障公民的利益与权利。[1]在刑事诉讼中,作为控方代表的检察官与被告人在参与诉讼的能力方面存在着较为严重的不平等的现象,这导致控辩双方诉讼地位的不平衡。为了使国家与刑事被告人能够进行理性的对话,宪政要求国家应当承担以积极作为义务的方式为刑事被告人设定某些特殊的程序保障措施,以达到矫正这种控辩不平等的状态,获得律师帮助的宪法权利就是矫正这种天然不平等状态的刑事被告人特权设置之一。正如有学者指出,加强对刑事被告人的特殊保护,使其拥有一些特权,表面上似乎会造成一种不平等:法官将天平一端倾向刑事被告人,并使其处于受保护的优越地位。但从根本上看,这正是为了克服控辩双方实质上的地位不平等而采取的措施,即以形式上的不平等来换取实质的平等。尤其是当我们注意到检察官地位的公正性、客观性和中立性会有一种不可避免的限度时,加强对刑事被告人的特殊保护就更应被视为一种对控辩双方地位的主要平衡手段。[2]
在刑事诉讼中,对于实现程序公正而言,律师辩护是一项不可或缺的制度。尽管人们对程序公正的标准未达成一致见解,但无论是在“自然正义”的古老原则中,还是在“正当法律程序”的宪法条款里,都把刑事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权视为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律师辩护在实现程序正义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第一,控辩双方平等对抗,是现代刑事诉讼中的基本格局,也是刑事司法中体现程序正义的重要方面。刑事被告人获得律师有效帮助是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拥有平等地位的基础,也是审判中立的重要条件;第二,刑事被告人是刑事诉讼的核心人物,如何对待被告人是诉讼程序公正与否的重要标志。刑事被告人获得律师有效帮助使得被告人可以有效反对控方的指控,并对证据提出质疑并提出理由,使其能够富有成效地影响诉讼结局,真正的成为诉讼主体,而非控方和法官任意摆布的客体;其三,刑事被告人获得律师有效帮助有助于对国家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刑事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意味着被告人可以向司法机关提出异议,享有公平的辩护机会,这是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
二、美国刑事被告人获得律师有效帮助的宪法标准的演进
美国联邦宪法第六修正案规定:“在一切刑事案件中,被告人享有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Strickland诉Washington案中认为:“获得律师的权利就是获得律师有效帮助的权利”。所谓的律师有效帮助,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如何判断律师的帮助是否“有效”。就此问题,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经历了一个长期的争辩与演进,并在1984年产生比较明确统一的见解。
美国最高法院最早在Powell诉Alabama案中承认被告人有获得律师有效帮助的宪法性权利。十年以后,在Glasser诉United States[3]一案中,最高法院的判决认为在一个联邦案件中,如果某一司法行为否认被告人有权获得律师的有效帮助的话,则该行为已经违背了第六修正案的有关规定。在承认第一次上诉中被告人有平等的权利来得到指定的律师之后,最高法院认为提起这种上诉的被告人也拥有获得其上诉律师有效帮助的宪法性权利。在1970年以前,大部分法院对于律师有效帮助的判断标准是“荒诞剧和笑柄”的标准。根据Gideon案判决时的法律,法院认为,律师应提供有效的帮助,他们在法庭上代理行为不应是“荒诞剧和笑柄”式的代理。这一标准来自Betts诉Brady一案确定的公正审判的诉讼程序。在此标准下,被告主张未获得律师的有效帮助,必须证明审判是一场闹剧,极为困难。Gideon案后,许多人希望法院能够根据一个更高的标准来衡量律师的辩护行为,以提高辩护的质量。
在为改变律师代理标准的争论中,当事人及评论家们认为被告人应当有权得到一个合理、有能力的律师代理,而不仅仅有权聘请律师,法官们则不同程度地抵制了这些主张,法院不愿改变这一标准是基于对改革后果的忧虑。法院的这种担心主要理由有三:(1)如果律师的行为稍有瑕疵,上级审法院就必须撤销原审判决,将会破坏判决终局性,再者会造成法官过渡干涉辩护行为,法院只要怀疑律师的行为可能有瑕疵,即必须随时介入。(2)如果法院过于严格检验律师的代理行为,会导致律师不愿意接受法院指定的案件。(3)对于胜诉机会不大的案件,律师可能会故意犯错制造瑕疵,成为上诉翻案的原因。
克服了这种担心之后,法院最终开始倾向那些主张抛弃“荒诞剧和笑柄”标准的意见。在1970年的McMann诉Richardson案,提出所谓的“合理胜任”标准。在该案中,联邦最高法院指出,只要律师所提供的建议,是刑事辩护律师所认可的适当范围内,即为提供律师的有效帮助。
对于“合理胜任”标准,许多法官和学者批评其模糊不明确。联邦法官Bazelon又提出“逐项检查或类别化”标准,即先将律师应有的辩护行为予以逐项明示或类别化,并检视律师在个案中是否逐项做到应有的辩护行为,借此设立辩护人最起码应达到的最低标准,如未达到应有的最低标准,即视为未提供律师的有效帮助。此标准重视辩护人的行为表现,至于辩护行为是否会影响判决结果,在所不问。此标准获得众多学者的支持,但并未被大多数法院所接受。
在1984年的United States诉Cronic案[4]中的下级法院以行为本质来判断方法进行了引申,从而认为律师必然不能提供有效的帮助,即推论律师不能基于以下五种因素有关的情况而免除其责任:(1)可以用于调查和准备的时间;(2)律师的经验;(3)指控的严重程度;(4)可能的辩护理由的复杂程度;以及(5)律师接触到证人的可能性。史蒂文斯大法官在判决意见中认为,下级法院所采用的这种“推论方法”缺乏最高院过去的先例支持,并且与有效帮助要求的功能不一致。由此得知,律师帮助的无效性不能根据辩护律师以上标准进行推断。然而,在过去最高法院的判决中,史蒂文斯大法官发现在两种情况下这种推定的方法是才具有正当性:第一种情形是,“在诉讼的关键阶段,律师或者根本没有出庭,或者被阻止为被告人提供帮助”。第二种情形是,在某些的情况下“被告人在审判期间虽然可以得到律师的帮助,但是对于任何一个律师,甚至是一个相当优秀的律师,如果他能够提供有效帮助的可能是如此之小的话,即使在没有调查审判的实际活动时,也可以推定这是不公正的。”
1984年的Strickland诉Washington案[5],联邦最高法院终于确立此问题的宪法标准。Strickland诉Washington案表明,如果辩护律师有以下行为,其为被告人提供的帮助是无效的:(1)律师有瑕疵行为,没能有效的发挥作用;(2)律师所犯的严重错误对被告人造成了不利影响,且导致被告人无法获得公正的审判。1984年之后联邦最高法院还指出被告人未受律师的有效帮助有三种情形:(1)辩护人造成的错误。例如辩护人对重大法律不了解,影响被告权利的实现,就不是有效的律师帮助。(2)政府的干涉行为。例如在审判中休庭等待翌日继续开庭,禁止被告与律师会谈等,即为非法干涉辩护人的辩护行为。(3)利益冲突。例如辩护人同时为利害相反之二共同被告辩护,也不是有效的律师帮助。
在1993年的Lockhart诉Fretwell一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制定了更难以推翻定罪的标准,即根据Strickland案,为了表明审判不公,被告人必须证明辩护律师的错误是如此严重,以至于剥夺了他享有一个公正或可信赖的审判权,而不仅仅是审判结果不同。
三、刑事被告人获得律师有效帮助的制度功能
获得律师的有效帮助作为刑事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依法享有的一项诉讼权利,这对于被告人获得公平审判和实现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现代刑事诉讼中,辩护权被确立为一项基本人权,是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依法享有的最重要的权利,他们享有的其他诉讼权利,都与辩护权密切相关,离开了这个核心,其他权利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刑事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源于刑事被告人自身所享有的辩护权。“鉴于被指控人进行自行辩护的现实障碍,被指控人有权获得来自私人法律专家——律师的帮助。”[6]目前,几乎所有国家的宪法和刑事诉讼法均把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视为其最基本的诉讼权利。
根据西方法治国家的法治实践,当刑事被告人享有获得律师帮助权时,该权利应指获得有效的律师帮助。[7]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一案件中曾言:“如辩护人不能提供有效的法律帮助,与无辩护人无异。”[8]鉴于刑事被告人往往处于自由受到严重限制的被羁押状态,其所面对的是强大的国家公权力,另外,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发展日趋专业与精致,一个不熟谙法律但能言善辩者在古代社会尚能自行辩护,但在现代司法制度面前他将举步维艰。正因如此,如果没有律师的帮助,刑事被告人就不可能在与刑事追究者或指控者在对等的意义上充分有效地实现自己的辩护权。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Strickland案指出,宪法上被告受律师协助的权利,目的在确保当事人进行主义制度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因此判断律师协助是否有效,重点在于辩护人的行为是否破坏此一功能,致审判产生不正义的结果。换言之,美国宪法规定刑事被告人获得律师有效帮助的目的并不是促进律师代理质量的提高,而是保证刑事被告人能够获得公正的审判。在国际人权公约中,刑事被告人获得律师有效帮助被视为公正审判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律师给予刑事被告人的专业性帮助,不仅有利于辩护被合适地准备、提交和展开,而且它有利于保障刑事被告人的程序性权利得到切实的尊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律师被称之为“程序规则的看门狗”。[9]因此,刑事被告人获得律师有效的帮助的制度功能在于获得公正的法庭审判并避免受到不公正的定罪和判刑。
四、对美国刑事被告人获得律师有效帮助权制度的借鉴
在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均对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权作了规定并体现于相应的程序中。这表明,我国已经确立了获得律师帮助权所要求的基本内容,但这与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和西方法治发达国家所确立的有效辩护标准仍有差距,司法实践中还存在大量的问题和弊病,这些缺陷和问题足以对被告人获得律师有效帮助造成现实障碍。因此,我国在加强和扩充刑事被告人辩护权方面,有必要借鉴美国关于刑事被告人获得律师有效帮助的发展规律和经验。
第一,我国刑事被告人获得律师有效帮助缺乏宪法权利的制度设计。根据宪政理论,宪法与刑事诉讼法具有高度的关联,刑事被告人的一系列权利只有确立在宪法之中,上升到宪法性权利的高度,这些权利才会具备坚实的法律基础。但是从我国宪法的规定来看,仅仅将刑事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权作为法院审判工作原则,使得刑事被告人权利的维护缺乏宪法的具体依据。
第二,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被告人有权获得法律规定的强制辩护的关键阶段未作出具体的规定。根据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例,刑事被告人在关键阶段(critical stages)即那些缺少律师帮助将会影响到刑事被告人实体权利的阶段,都应当享有获得具有法律强制保障的律师帮助的权利。如果因经济困难无力聘请私人律师,则法院应当为其指定律师,使其享有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4条规定,被告人因经济困难,盲、聋、哑,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帮助。根据以上规定可知,强制辩护适用范围十分有限,在适用阶段上比如在第二审程序、死刑复核程序、再审程序以及执行程序中是否适用强制辩护没有明确规定。
第三,我国刑事诉讼法未明确被告人未获得律师有效帮助的法律后果,更未规定任何有效的权利救济措施。在美国,对于律师未能提供有效帮助的,二审法院可以依此发回一审法院重审,甚至可以改变对被告人的有罪判决。[10]在我国,尽管由于诉讼模式和诉讼结构的不同决定了律师在诉讼中对诉讼结果的影响力比起美国而言要小,但如果律师疏于履行职责或者政府未指定律师帮助造成了对被告人不利的后果,则该不利后果就不应当由无辜的被告人来承担。
有鉴于此,我国应当借鉴美国经验,将刑事被告人获得律师有效帮助权上升为宪法性权利,为未来的刑事被告人获得律师的有效帮助提供足够的宪法支持,以对刑事被告人获得律师的有效帮助提供切实保障,明确规定强制辩护的关键阶段以及律师无效辩护的法律后果,确立完善的审判前阶段被告人获得律师有效帮助的权利和法律援助制度,确立刑事被告人获得律师有效帮助的救济权利,明确律师未提供有效帮助的程序后果,比如一审被定罪的被告人以未获得律师有效帮助为由提出上诉,二审法院经审查后,如果认为理由成立,应撤销原判,将案件发回重审。
【参考文献】
[1] 夏勇等:《中国当代宪政与人权热点》,昆仑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2] 陈瑞华:《刑事审判原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61页。
[3] 315 U.S. 60, 62S. Ct. 457, 86 L. Ed. 680 (1942).
[4] 466 U.S. 648, 104 S. Ct. 2039, 80 L. Ed. 2d 657 (1984).
[5] 466 U.S. 668, 104 S. Ct. 2052, 80 L. Ed. 2d 674 (1984).
[6] 谢佑平、万毅:《刑事诉讼法原则:程序正义的基石》,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293页。
[7] 周宝峰:《宪政视野中的刑事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权研究》,载于《内蒙古大学学报》,2009年7月,第41卷,第4期。
[8]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85年Evitts诉Lucey案中指出。
[9] See Stephanos Stavros, The Guarantees for Accused Persons under Article 6 of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1993,p.202.
[10] 此种有罪判决的撤销具有严格的条件限制。最高法院在Stickland 案中明确表示,对于实际上无效的律师的诉求应从两个方面来考察:第一,被告人必须证明根据通行的职业准则所确立的有关合理性的客观标准来衡量,律师的表现是失败的。第二,被告人必须证实,存在着这样一个合理的可能性,即如果不是律师的非职业性错误,诉讼结果会完全不同。参见威廉 J.盖乃哥:“有效的律师协助的未来——代理行为、标准及有能力的代理”,苗红环译,载江礼华、杨诚主编:《美国刑事诉讼中的辩护》,第180、185页。